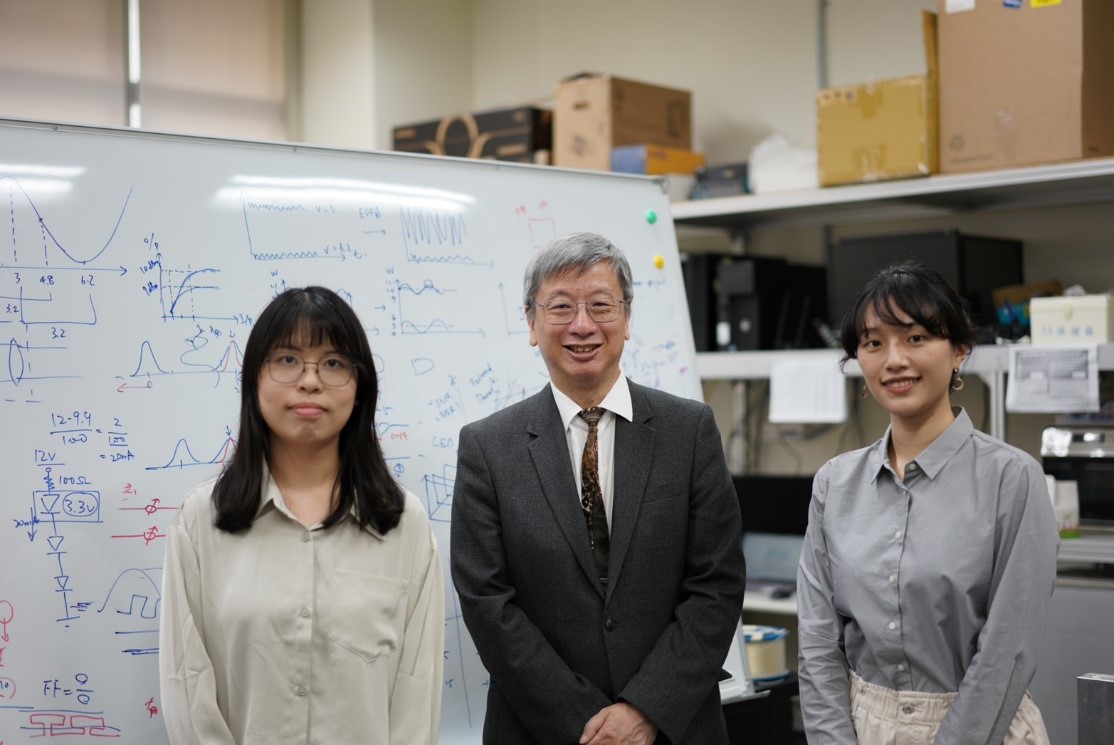曾漢奇教授專訪
訪談:張芯瑀、陳宜榆 / 文:陳宜榆
曾教授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光學積體電路(photonic integrated circuits),特別是應用於高容量資料中心光學互連的矽光子(silicon photonics),以及用於光感測與成像的矽光子技術。他的研究團隊專長於先進波導光柵耦合器(waveguide grating couplers)技術,透過光刻製程(photolithographic patterning)及商用矽光子代工廠標準的 PDK 流程,實現了超寬光頻帶(>150nm)及極低損耗(每個介面 <1dB)的紀錄。目前進行中的研究計畫包括:可重組矽光學積體電路、光學材料與矽光子的混合整合(hybrid integration),以及用於量子通訊、量子計量與量子運算的整合型量子光子裝置。
二十年前矽光子還未崛起,您當時就開始著手於矽光子的研究。想請問您是如何發掘這個領域的潛力?
做研究其實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觀察人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然後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這種是應用型研究,具有非常明確的目標,即尋找解決特定問題的新方法。另一種則是出於好奇心而進行的研究。這種好奇心驅動的研究是針對某種材料或系統提出問題,看看是否能對其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開始投入矽光子學研究的契機,其實是從事砷化銦鎵磷(Indium Gallium Arsenide Phosphide)半導體波導的研究開始的,並不是矽,研究這些材料大約有六、七年。我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也在英國的巴斯大學擔任過博士後研究員,並且曾拜訪美國的貝爾實驗室。我們當時嘗試使用 III-V 族的半導體波導來製作光學元件,例如可調式濾波器,或使用全光開關技術進行光學切換,但在研究 III-V 波導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強烈的雙光子吸收(two-photon absorption)與自由載子吸收(free carrier absorption)。另一個很大的挑戰是難以垂直蝕刻,導致很難精確控制元件的尺寸與反射的特性。
後來我讀到一些論文指出,矽是一種技術更為成熟的半導體材料,可以實現非常垂直且精確的波導蝕刻。當時我心想:如果能這麼輕易地製作出理想的波導,蝕刻垂直、完全符合設計,那麼我就想知道,它是否也會像 III-V 波導一樣,存在著雙光子吸收與自由載子吸收的問題。大約在西元 2000 年左右,我開始投入矽波導的研究,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我做了一些基礎實驗,觀察矽波導中的非線性效應,來驗證我的假設是否正確。
在進行這項研究的過程中,我讀到一位 UCLA 教授的理論預測,指出矽可以用來製作光放大器。這位教授是 Bahram Jalali,他提出如果對矽波導進行激發,由於矽是晶體結構,可以產生很高的拉曼增益,進而可能做出光放大器。他也針對這個理論發表了一篇以理論為主的論文。我看了那篇文章,心想:「等等,這好像哪裡不對。」因為在矽中會有雙光子吸收和自由載子吸收,這些非線性的損耗會增益。我接著用脈衝激發做了一些實驗,證實了我的懷疑。這是我早期的一篇論文,也成為被引用很多的研究,因為我們是第一個指出矽光子具有高度非線性,但也伴隨高雙光子吸收與高自由載子吸收,限制了可以傳入矽波導的光功率。這就是我進入矽光子領域的起點,接著開始研究如何改善矽光子技術,包括晶片與光纖之間的耦合問題。
The surge of significance of silicon photonics
我們研究團隊後來也開始投入矽調變器的研究。儘管整個平台在製造元件方面變得容易許多,但這項技術仍然存在許多挑戰,而這正是讓我們覺得有趣的地方——去嘗試解決這些問題。隨著時間推移,我指導過將近十位、甚至超過十位博士生在這個領域進行研究,涵蓋了拉曼放大器、光柵耦合器、光開關調變器、折射率感測器、環形共振腔等多種元件的開發。因為我們是亞洲、甚至全球最早一批投入這些領域的研究團隊之一,而矽光子學這個領域,目前也發展成為非常豐富而有潛力的學術研究。從最初只是出於好奇、屬於”blue sky research”為起點 (指發展當下沒有顯著產業應用的研究),經過 25 年的發展,矽光子技術已經開始在現實中產生一些重要的應用成果。
它現在其實已經成為網際網路運作方式的基礎。如果你觀察網路的流量模式,大多數的流量,可能高達 90% 以上都會進入資料中心。流量之龐大,如果資料中心無法即時處理這些,透過網際網路傳輸的資料封包,就必須將這些資料丟棄並重新傳送。這樣的延遲效應類似於對網路伺服器發動的阻斷服務攻擊(Denial-of-Service,簡稱DoS),整個網路可能因此崩潰,而整個系統就會全面失效。但幸運的是,矽光子收發器(silicon photonics transceivers)具備多個資料通道整合於單一晶片中,能夠處理龐大的流量。有了這些收發器支援資料中心,網際網路的流量才能持續成長、不中斷地運作。
另一個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的矽光子新興應用,是所謂的「共同封裝光學」(Co-Packaged Optics,簡稱 CPO)。如果你有看 NVIDIA 的相關資訊,他們在 YouTube 上的 GTC(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演講中也提到,他們正推動此技術發展。他們利用矽光子技術來大幅降低功耗,在 GPU 與 GPU 之間的連接中,預計能減少達 3.5 倍的功率消耗,同時提高資料傳輸容量,以支援更大的資料量與更高的效能。這項技術正逐漸成熟,可以想像在不久的將來,每一顆 GPU 都會搭配一個共同封裝的矽光子晶片,負責資料傳輸作業。這將成為推動 GPU 所帶動的 AI 革命的關鍵基礎之一,需求量也將非常龐大。因此,矽光子不僅已成為支撐網際網路的核心技術,未來在人工智慧與 GPU 領域中也將扮演關鍵角色。
最近在香港,我和我的博士生們成立了一家矽光子領域的衍生公司 Optik。這家公司在兩個月前才剛開始營運,但我們已經成功為未來三年募得了 700 萬美元的資金。
這筆資金來源是三分之二來自香港政府的資助,三分之一則來自投資者。我們公司目前專注的領域,正是我先前提到的資料中心用的矽光子收發器,以及共封裝光學(Co-Packaged Optics)技術。
我們也在致力於將矽光子技術用於光譜儀的開發,目的是實現在晶片上測量光的光譜。光譜儀在許多應用中都非常關鍵,例如光學相干斷層掃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在 OCT 中,取得3D影像的方法之一,就是使用寬頻光源,例如 LED。而當光源的頻譜越寬,其「同調長度(coherence length)」就會越短,短到甚至小於一毫米的一小部分。舉例來說,若使用一顆光譜寬度為 80 奈米 的 LED 光源,便能夠將成像深度提高到幾微米等級。因此,光學相干斷層掃描(OCT)其中一個重要應用,就是用來觀察眼睛,或檢測皮膚下的組織,例如用於皮膚癌的早期偵測。我們的夢想是打造一台 小到晶片等級的OCT 儀器,並整合進手機中。未來只要用手機掃描,就能檢測皮膚底下是否有癌變組織。
但同時,我也必須說,目前培養矽光子設計人才的學校仍然不多。在業界,企業要找到有經驗的矽光子設計工程師其實相當困難,整體人才供應呈現出明顯的短缺。
我自己的研究團隊約有 10 位博士生,他們很容易就找到了矽光子設計方面的工作。我們的校友目前有人在美國的 Cisco、Intel、Lumentum 等公司從事矽光子相關工作。此外,最近我在香港創辦的這家新創公司,也一次網羅了我指導的 6 位博士生一起加入,成為這家公司的創始團隊之一,也有將公司的股份分給他們,希望能激勵他們憑藉這項技術,打造出下一家矽光子領域的前導公司。
這就是我的夢想,這項技術能夠成功,或許未來就像 Qualcomm 一樣,甚至像我剛才參觀過的 聯發科(Mediatek),它是一家在台灣成長茁壯的傑出 IC 設計公司。而我們的公司 Optik,也許未來也能走上相同的道路,成為像聯發科那樣的企業,只不過我們是專精於矽光子晶片設計,開發出無數優秀的設計。
我認為,這條路線是有可能並行發展、相提並論的。
如今,雖然已有一些代工廠可以製造矽光子晶片,但能夠從事這些晶片設計的公司或人才仍然相當稀少。設計公司越多,我們就越能針對不同應用場景,開發出對應的矽光子解決方案。矽光子技術不僅能應用在資料通訊領域,還可以廣泛應用在其他技術上,例如:成像與 3D 影像技術、工業量測(Industrial Metrology)、光達系統(LiDAR)、光纖陀螺儀(Fiber Optic Gyroscopes)、甚至是 訊號處理(Signal Processing)的部分。
台灣目前仍然以積體電路(IC)設計為主要發展焦點,對於矽光子這個領域還不算是主流話題。它尚未成為主流,但正處於快速崛起的階段。
你可以想像,如果你在 1985 年畢業,有人告訴你應該進入 IC 設計領域,然後當時美國剛好有一家名叫 Qualcomm 的公司,只有七個人剛創立,他們提供你一份工作,並說:「我們會給你 Qualcomm 10% 的股份。」
如果你能想像那樣的情境,這就是現在矽光子產業的樣子。
這是一個機會,只要你願意跨出那一步,加入一家新創公司、承擔風險,並努力讓它成功。也許你只能拿到 5% 或 2% 的股份,但如果公司最後壯大、成功上市,10 年、15 年後你可能會非常富有。就像聯發科(MediaTek)或其他類似公司一樣,矽光子也可能孕育出下一個技術奇蹟。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相似的情勢。
Applications in the industry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確實存在許多機會。如果你有在關注相關新聞,像是在 Computex 展會上,NVIDIA 公布了他們正在推動建立一個共同封裝光學(Co-Packaged Optics, CPO)的產業聯盟;同時,Intel 也發起了另一個競爭性的 CPO 聯盟。綜觀業界變化,再回過頭來審視目前的技術,就會發現:不論是 NVIDIA 的聯盟還是 Intel 的聯盟,其實都還沒真正解決互連(interconnect)中最關鍵的問題——頻寬密度(bandwidth density)。
現今的電子 GPU,對資料傳輸的需求非常驚人,每毫米邊緣長度就可能需要超過 20 Tbps(Terabits per second)的頻寬。而目前的實作方式,是從晶片邊緣引出光纖傳輸資料。但如果觀察晶片的尺寸,會發現最大的限制是:每毫米晶片邊緣所能傳輸的資料量。舉例來說,像 Broadcom 推出的 UCIE(Universal Chiplet Interconnect Express)技術,它的規格是每毫米 1.3 Tbps,這比實際所需的頻寬低了約十倍。
因此,現在的產業發展與實際技術需求之間,仍存在明顯落差。
簡而言之,目前仍存在許多尚待解決的挑戰,有些或許能透過良好的矽光子設計來克服。儘管有許多公司正嘗試解決這些問題,但還是有很多機會讓聰明的博士生與博後研究員,提出出色的解決方案。這也是我們這家小型新創公司的定位:瞄準那些尚未被解決的技術縫隙。
To be a bit more specific, a lot of your early work centers around nonlinear properties. We've learned in class that for nonlinear properties to exist, you would need to have a very high intensity, or high energy density input.
更具體來說,您早期的許多研究集中在非線性特性上。就我們課堂所學,要產生非線性效應,通常需要非常高的光強(強度)或高能量密度的輸入。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我上個月在美國參加了一個名為 CLEO(Conference on Laser and Electro-Optics)的會議。其中一場專題演講提到了單光子非線性光學(single photon nonlinear optics)。在量子光子學(quantum photonics)的脈絡,單光子概念是這樣的:如果你產生一個非常短的光脈衝,並將其脈衝寬度縮短到飛秒(femtosecond)等級,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只會有一顆光子。當你計算這顆光子在飛秒尺度內所攜帶的能量,並以 PAR(power-average rate,即能量/時間)來表達,由於時間單位非常短(飛秒),因此它的峰值強度(peak intensity)會非常高。若將此單光子脈衝耦合到200 奈米尺寸的波導內, PAR會變得非常高,從而進入高度非線性的光學效應領域。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所謂的「單光子」系統,也可能在極短時間、極小體積內產生顯著的非線性光學效應。
如果有一個非常短的脈衝,即使是單顆光子進入,就已經可以觀察到非線性效應了。
需要先釐清的是:什麼是光子?光子並不是由單一波長來定義,也不僅是一個微小的粒子。事實上,光子可以擁有很廣範圍的波長,甚至可以涵蓋 20、30、40 或 50 奈米 的波長範圍,仍然可以被視作同一顆光子。因此,光子不必然是純粹的單頻波,這對我們來說是全新的觀念。換句話說,光子可以是一顆帶有波長分布的粒子。
我認為,未來看到光子學被應用的另一個重大方向,將會在量子運算或量子資訊處理領域。在量子力學裡,有波粒二象性的概念。與其像麥克斯威爾方程那樣將光看作波,你可以把光看作粒子。這樣一來,當你將一顆光子送入矽波導時,就能與矽材料系統中的電子互動,把電子激發到較高的能階。接著,電子會從高能的虛態(virtual state)回到它原本的能階,並再度釋放出那顆光子。
不過在量子力學中,電子從虛態回到基態時,可能會釋放出兩顆光子,而這機率並非為零。這只是模擬出來的嗎?不是的,這就是所謂的自發型參數性下轉換(spontaneous parametric down-conversion, SDPC),屬於二階效應(second-order effect)。同樣地,電子也可能吸收兩顆光子,躍遷到高能態,然後再返回基態,同時釋放出兩顆光子。有趣的是,這兩顆發射出來的光子,不一定要與最初被吸收的兩顆光子完全相同。它們的波長可以略有不同。舉例來說,假設你將一束 1550 nm 的連續光波輸入到矽波導中,它會將電子激發到高能態。當電子再回到低能態時,會釋放出兩顆光子。這兩顆光子不一定都恰好是 1550 nm,可能是一顆 1549 nm,另一顆 1551 nm,只要它們的總能量與原先被吸收的能量相同,就滿足能量守恆。這代表你可以藉由這個過程,從兩顆獨立的光子生成一對光子對。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這對光子是同時被發射出來的,因此在時間上是相關的。還有一點需要理解的是,它們其實處於一種糾纏態(entangled state),是單一的疊加態。即使它們看起來是兩顆可以前往不同地方的光子,但如果對其中一顆光子進行測量,就會影響到另一顆光子。這就是量子效應中的非局部效應(non-local effect),也就是你在實驗室中對一顆光子做測量,卻會影響到另一個相距 10 公里之外實驗室中的那顆光子。(量子遙傳,quantum teleportation)這種現象在量子資訊處理與通訊上非常有用,甚至可以利用它來設計演算法進行量子模擬。而且這也是一種在矽波導中非常容易觀察到的。
目前已經有幾家公司投入這個領域,例如矽谷的 SciQuantum、加拿大的 Xanadu,它們各自已募得超過 2.5 億或甚至 8 億美元的資金,正試圖發展用於量子資訊處理的矽光子技術。這項技術可能會在五到十年後真正成熟,成為矽光子領域的下一波應用。矽光子不只是用於資料中心、GPU、高速收發器、光譜儀、OCT,或是 LiDAR 的相位陣列,它還能在量子通訊與量子運算的領域發揮作用。這可能成為下一代量子運算的基礎,也是極為新穎的研究方向。
What we've learned in class is that transatlantic fibres, they used to be transatlantic. The main goal would be to minimize the loss because it needs to transmit at a long distance. But now in data centers, they're transmitting in short distances, but we need to maximize the data we can transmit at a given time. Our next question would be, with this change, what was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optical transmission?
我們在課堂上學到,過去的跨大西洋光纖主要目標是盡量降低損耗,因為需要傳輸很長的距離。現在在資料中心中,傳輸距離雖然很短,卻需要在同樣的時間內傳送盡可能多的資料。我們下一個問題是:隨著這樣的改變,這兩種光傳輸(長距離 vs 短距離高資料率)之間有什麼不同?
電信領域的長距離通訊,通常是使用 1550 nm 波段,因為在過去,這是石英光纖損耗最低的波長範圍。而在資料中心,則通常採用大約 1310 nm波段,這是因為在此波長附近,光纖的色散(dispersion)為零,非常適合用於高速通訊。光學色散是指,當傳送一個短脈衝或一串短的數據脈衝,例如 200 Gb/s,其時間窗大約只有 5 皮秒(ps) 左右。根據時間-頻寬乘積(time-bandwidth product),這樣的脈衝會對應到一個相當寬的頻譜。如果在傳輸過程中有色散,就會造成脈衝中的短波長與長波長部分在傳輸後發生相位差,進而在某些距離產生破壞性干涉(destructive interference),形成傳輸窗口的凹陷,最終導致錯誤的資訊發生。因此,對於高傳輸速率和長距離光纖傳輸而言,色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資料中心的收發器都選擇在大約 1310 nm 這個波長工作的原因。
現在有一項新興技術叫作空心光纖(hollow core fiber),它不像傳統光纖那樣使用玻璃作為核心,而是採用中空結構,並利用反共振(anti-resonant) 的設計來導光。最近有研究報告指出,這類空心光纖的損耗已經比傳統玻璃光纖還要更低。這代表我們未來有可能可以在光纖中選擇承受最高功率的波長來運作,不再一定受限於 1550 nm。
The importance of reducing insertion loss
我們已經發表了可達 90 GHz 以上 的資料,並且在已發表的成果中,實現了 PAM-8 調變器(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8)高達 330 Gb/s 的數據傳輸速率。不過,我的學生們還有一些尚未發表的研究,數據已經超越了這個水準。我們每次都在不斷推進技術的極限。不過,一直強調資料速率反而忽略了真正的重點。光柵耦合器(grating couplers)上目前看起來比較不起眼的研究其實是重要的。它是用來將光從晶片耦合到單根光纖的裝置,幾乎每個人都會用來做測試,乍看之下似乎沒什麼特別,就是把波導裡的光,透過繞射(diffraction)耦合到光纖。
但如果對這些系統有更多了解就會知道,光纖與晶片之間的耦合損耗,其實才是矽光子技術中最關鍵的問題。插入損失(insertion loss) 會影響許多層面。在一個收發器或網路系統中,真正需要的是能夠支援許多平行資料通道(parallel data lanes)。舉例來說:一個典型的收發器會使用多色帶光纖(multi-ribbon fiber),在可插入收發器和 MPO 連接器中,會有 8 根光纖輸入、8 根光纖輸出。只用一個雷射,將光分成 8 個通道,在每個通道上調變不同的資料通道的訊號。如果每個通道可以達到 200 Gb/s,那麼透過 8 個光纖,你就能用一個雷射達到 1.6 Tb/s 的總傳輸量(8 × 200 Gb/s)。
問題就出在這裡:如果調變器本身已有 6 dB 的插入損失,再加上每個光纖到晶片的耦合點又有額外 3 到 4 dB 的損耗,每個調變器的整體損耗就差不多會來到 10 dB。這樣會發生什麼事?假設你用一顆雷射輸出 100 mW,然後經過 1-to-8 的分光器,每條通道就只剩下 12 mW。再經過調變器與光纖耦合帶來的超過 10 dB 損耗(也就是功率大約少了 10 倍),最後剩下不到 1 mW 能送入光纖。如果每個地方的損耗再多個 2 或 3 dB,那麼可能就只剩下 0.5 mW,這樣的功率已經不足以支援資料通訊所需的接收靈敏度。
接下來為了因應損失,得將收發器內的雷射數量從 1 顆增加到 2 顆,甚至 4 顆。但這會產生下個問題:每顆雷射都可能成為收發器的單點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如果你的收發器裡有 4 顆雷射,那麼只要其中任意一顆失效,整體系統的可靠性就會下降,增加實際使用時發生故障的機率。所以,這一切最終都會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如何降低光纖耦合損耗以及插入損耗,這才是決定整個收發器效能與可靠性的關鍵。
這也是為什麼,對於我們團隊在標準光柵耦合器(grating coupler)上做到小於 0.9 dB 的損耗,也就是所謂的次分貝(sub-decibel)損耗,我會感到自豪。這可能平時聽起來沒什麼特別的,但如果了解它對整個系統的影響,就會知道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技術。同時我有特別要求學校替我們申請專利,而有些晶圓代工廠(foundries)甚至主動聯絡我們,希望能夠取得授權,這也證明了這項專利的價值。從一般角度來看,可能有人會覺得:「哦,不就是另一種光柵耦合器嗎?做到低損耗似乎也沒那麼了不起。」但實際上,這正是一項矽光子技術的核心關鍵。
這也是為什麼,對於我們團隊在標準光柵耦合器(grating coupler)上做到小於 0.9 dB 的損耗,也就是所謂的次分貝(sub-decibel)損耗,我會感到自豪。這可能平時聽起來沒什麼特別的,但如果了解它對整個系統的影響,就會知道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技術。同時我有特別要求學校替我們申請專利,而有些晶圓代工廠(foundries)甚至主動聯絡我們,希望能夠取得授權,這也證明了這項專利的價值。從一般角度來看,可能有人會覺得:「哦,不就是另一種光柵耦合器嗎?做到低損耗似乎也沒那麼了不起。」但實際上,這正是一項矽光子技術的核心關鍵技術。
另一方面,高速調變器(high-speed modulators)其實只要有適合的設計,再加上可以使用對應製程的代工廠,比較容易做得出來。在設計上比較棘手的,其實就是決定環形共振腔的長度,以及環與波導之間的間隙。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在布局中直接控制的參數。對於一個微環調變器,需決定的環的半徑和環與波導間的間隙,依照計算出來的彎曲損耗(loss by bending radius)與長度損耗,就可以進行設計,讓它運作起來。如果你能夠用模擬工具跑出結果,要設計一個 300G 或 400G 的調變器,其實是完全可行的。只要有合適的工具,這並不是什麼難以突破的門檻。
但要創造出創新的光柵耦合器,需要真正的理解背後物理的運作原理。很多人嘗試用反向設計(inverse design)方法來做光柵耦合器,能做到大約 1~2 dB 已經算很幸運了,而且通常必須做到 20 或 30 奈米等級的特徵尺寸,製造上非常困難。我們的設計只需要 170 奈米的特徵尺寸,就可以在代工廠大量製造,而且還能保持高良率、低損耗。很多人會對那些極高資料傳輸速率的結果印象深刻,但如果不把損耗降下來,終究還是會受限於損耗。損耗通常才是整個系統的真正瓶頸。
功率、損耗、可靠性,這一切最終都與插入損失相關。如果你能在光學積體電路中把插入損失降到最低,就會帶來許多好處,因為這是整個系統中最重要的指標。這也是我從產業界學到的第一課。一開始可能覺得「損耗」聽起來沒什麼大不了,人們會想:「啊,多了 1 dB 的損耗,多花 20% 的功率就可以了。」但實際上,一旦把整個系統預算(power budget)攤開來看,這裡 1、2 dB,那裡再 1、2 dB,很快就累積起來。這是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理解的重要經驗:損耗就是一切。如果損耗太大,那基本上所有努力都白費,因為把大量能量白白丟掉了。
How might these theoretical discoveries be related to applications, like in data centers or such things?
這些理論上的發現,會如何與實際應用產生關聯,比如說,在資料中心或類似的場域裡?
目前在資料中心、共同封裝光學、以及光譜儀方面所做的理論研究,大多都是非常以應用為導向的,背後都有明確的工程應用需求。另外,還有一些有趣的研究,像是在積體量子光學(integrated quantum photonics)領域,包括產生壓縮光、以及建立 2、4 或更多光子糾纏叢集態(cluster states) 的實驗,這些都還停留在物理層級的探索階段,主要目的是想看看能否做出高效的電路,用來生成量子模擬所需的叢集態。目前還無法進入實際應用,因為還有一些關鍵問題尚未被解決,像是如何進一步提高量子干涉的能見度。如果未來能夠克服這些挑戰,那將會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發展方向。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量子光學的領域,損失也是極為關鍵的問題。如果產生了一對糾纏光子,但其中有一顆因隨機散射而遺失,那麼它們就不再糾纏了。因此,在積體量子光學電路中,如何盡可能降低損耗以建構高傳真度(high-fidelity)的量子電路,也是極其重要的課題。這對於非線性量子光子學與線性量子光子學來說是一樣重要的。還有一些其他有趣的應用。例如,晶片上的干涉儀(interferometers),以及先前提到的 2x2 光耦合器(two-by-two couplers),都可以用一個 2x2 矩陣 在數學上來描述。這樣就可以在它們上面進行單一矩陣(unitary matrix)運算。在線性代數中,單一矩陣很容易算出反矩陣。在光學中,我們就能藉由這些裝置實際執行單一矩陣運算。這對於光學訊號處理非常有用,例如可以進行矩陣乘法,或對訊號做串音(crosstalk)打散與重整,基本上就是用光學方式來解決一些數學問題。現在已經有人開始用此概念來消除串擾(unscrambling crosstalk),像是多輸入多輸出(MIMO)訊號處理。同樣的概念,也可以延伸應用到類神經運算網路(neuromorphic networks)或卷積(convolution)裡的矩陣運算。